|
吴纪珍女士的新作,“秋来了”
秋风萧瑟,黄叶落地,草木枯萎,眼看2017年即将迎来尾季的冬雪,在白净的雪花纷飞中无声无息的消逝...。 九月底的秋夜开始转凉,睡前总是听到窗前风铃清脆的声响,夹杂千百树叶的婆裟弄声,起风了,莫不过是要催促人儿早睡,早一点儿进入温醇的梦乡。晨起遛狗儿,我突然想起已过世近20年的外婆。其实我与外婆并不亲近,「威严」一字来形容不识字的外婆是最恰当不过!看著人家的眷村姥姥们和蔼可亲,笑容可掬,我这位外婆一句国语都不会讲,我看她,她看我,祖孙俩像个外星人。我的河南父亲身材高大,外婆总用著闽南话在舅舅们面前称我爸爸「大颗呆」,就是「又大又笨」的意思,四岁的我,小手插在腰上,对著大人用闽南语说著:「我爸爸不是「大颗呆」,不能这样叫他!」。外婆一脸尴尬,从此不在孩子面前这样称呼我的国军父亲了。 重男轻女的外婆把父亲孝敬给她的钱送哥哥上宜兰的幼稚园,骑著叁轮车的阿伯,後车箱里载著穿著围兜兜小围巾的幼儿群,我追上去就被舅妈拦住,舅妈抱著我,轻声的说:等妳回台北後,叫妳爸爸让妳上学去。外婆一听这话儿,马上回话:女孩子迟早要嫁人,读到小学识字就可以,识字後就找工作赚钱供她哥哥完成学业。外婆喜欢种花,一整天有做不完的事情,曬萝蔔,摘葡萄製酒,养鸡鸭,餵猪...。去庙会拜拜或探望姨婆,她总是带著我,姨婆嫁给耕农户,明朝式建築的四合院前院就是曬榖场,四面的稻麦在黄昏後随著晚风ㄧ波波吹起犹如金黄色的波浪般舞动,偶尔听著日式蒸气火车「喔....喔.....」驶过,姨婆跟我说她从来没搭过火车,和外婆ㄧ样都是文盲。 秋风吹叶黄的景象让我想起外婆的长髮,当时50多岁的她正如我现在的年龄,微捲不见白的长髮,手指ㄧ捞就变得这麽ㄧ小撮,外婆总是小心翼翼的梳妆,深恐无情的光阴再次让面貌腿色,我坐在小板凳上闷不吭声,看著外婆井然有序的拿出小木盒,摆出梳子,髮夹,塗脸白粉,她背对著我,两只手膀子不停摆动,梳理,那一幕就这麽烙印在我内心深处,时间也在记忆中停顿。至今浮现在我脑海仍是外婆那一波波的大捲长髮,我自幼以来就没见过外公与外婆同床共枕过,外婆在家中永远是以强势姿态发号司令,没见过她流过泪,只有一次是因爲母亲患病,不认她为母而落泪,外婆看著我,用微笑安抚母亲,双眼泪水盈眶,静静的离开眷村家门。外婆没有任何首饰,只有她母亲留给她一个沉灰色的玉镯,她把不起眼的玉镯切割四份留给女儿们,母亲过世後,我又把那小块玉镯段镶金成了玉坠子,很少戴它。 除了把新台币纸钞用报纸包起来藏在屋樑上,外婆出门时,也把纸钞捲成圆筒状,再用手帕捆捲包好,塞到旗袍包扣内,记忆中,外婆从来没买过零食给我吃,但是很捨得替孙子算命。母亲过世一年後,小舅「马沙」骑摩托车在工作路上被沙石车撞死,留下叁名幼子,舅舅,舅妈们隐瞒外婆我母亲过世的消息,怕她90高龄过度悲伤,因爲一年不见母亲,她就问道:阿琴怎麽没回宜兰来看看?小舅的丧事办完後,她把一生的积蓄一万五仟美金(新台币70万)全交给小舅妈,说著:一个女人家自己照顾叁个幼子很不容易....,真得很不容易。踌躇了一会儿,外婆又问:「昨晚我梦见马沙跪在我面前,肩上披麻带孝,我在想他是为谁披孝麻布敬跪在我跟前呢?」,舅舅、舅妈们望著苍老的外婆一语不发.....。 多少个秋天过去了,叶落多年总不断,人事变迁亦不止,留下来的仅是段段回忆,正如那无力又无奈的片片落叶......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平沙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元朝 马致远 Comments are closed.
|
Archives
July 2024
|
此网页所有版权为丹佛华人资讯网所有。 有对网页有关的问题请于[email protected]联络网页编辑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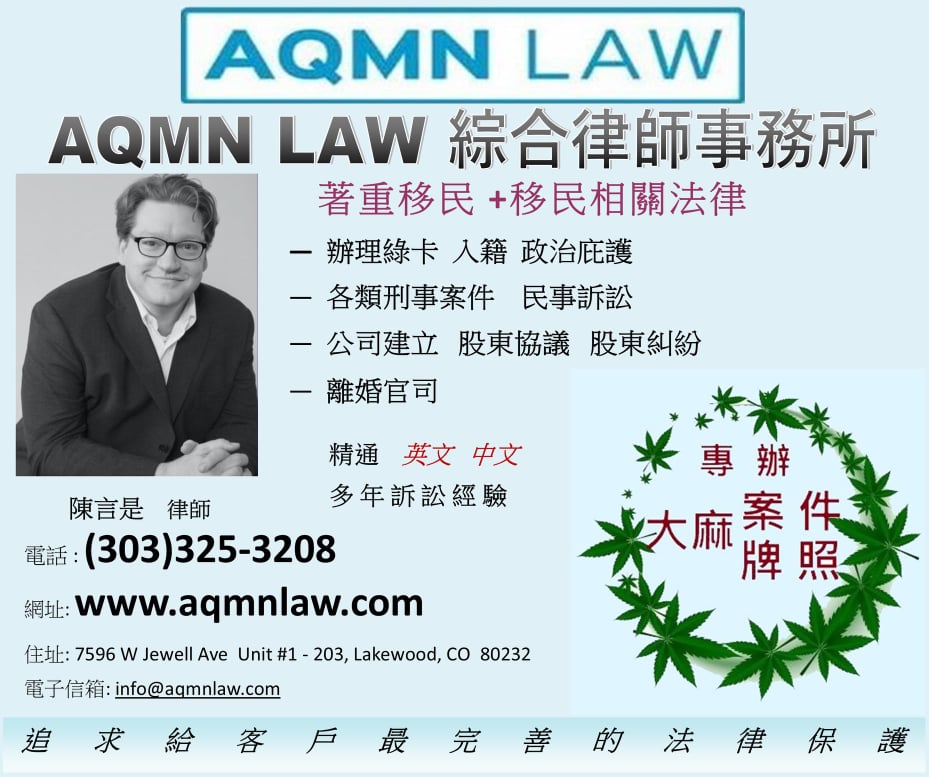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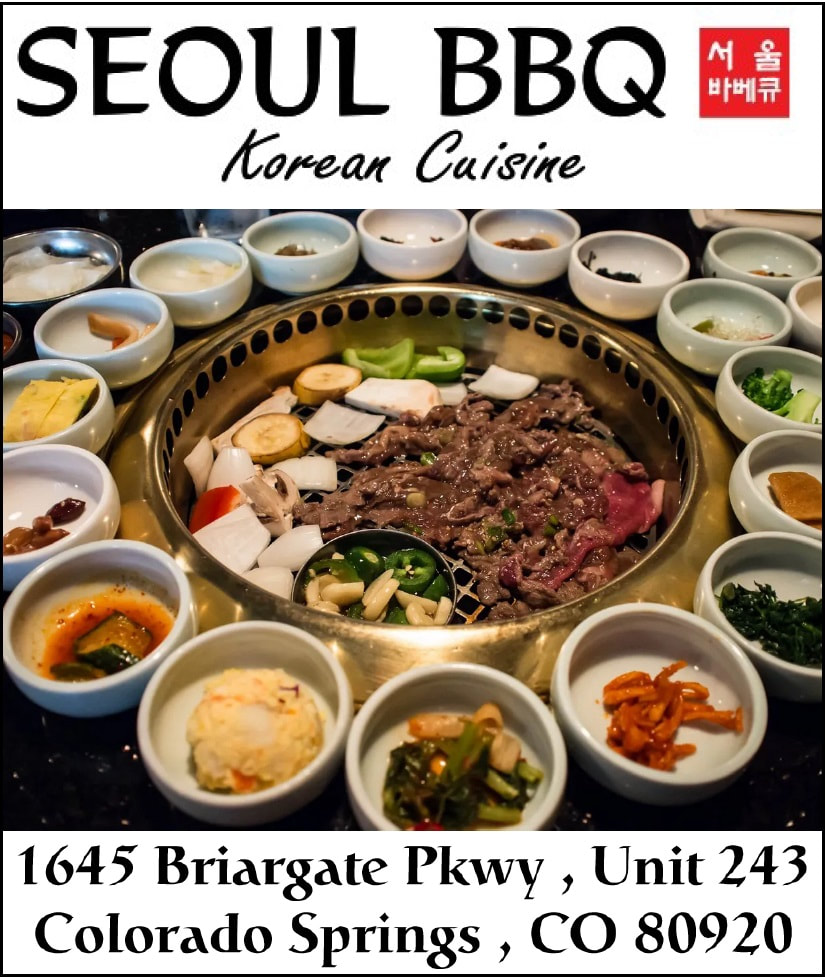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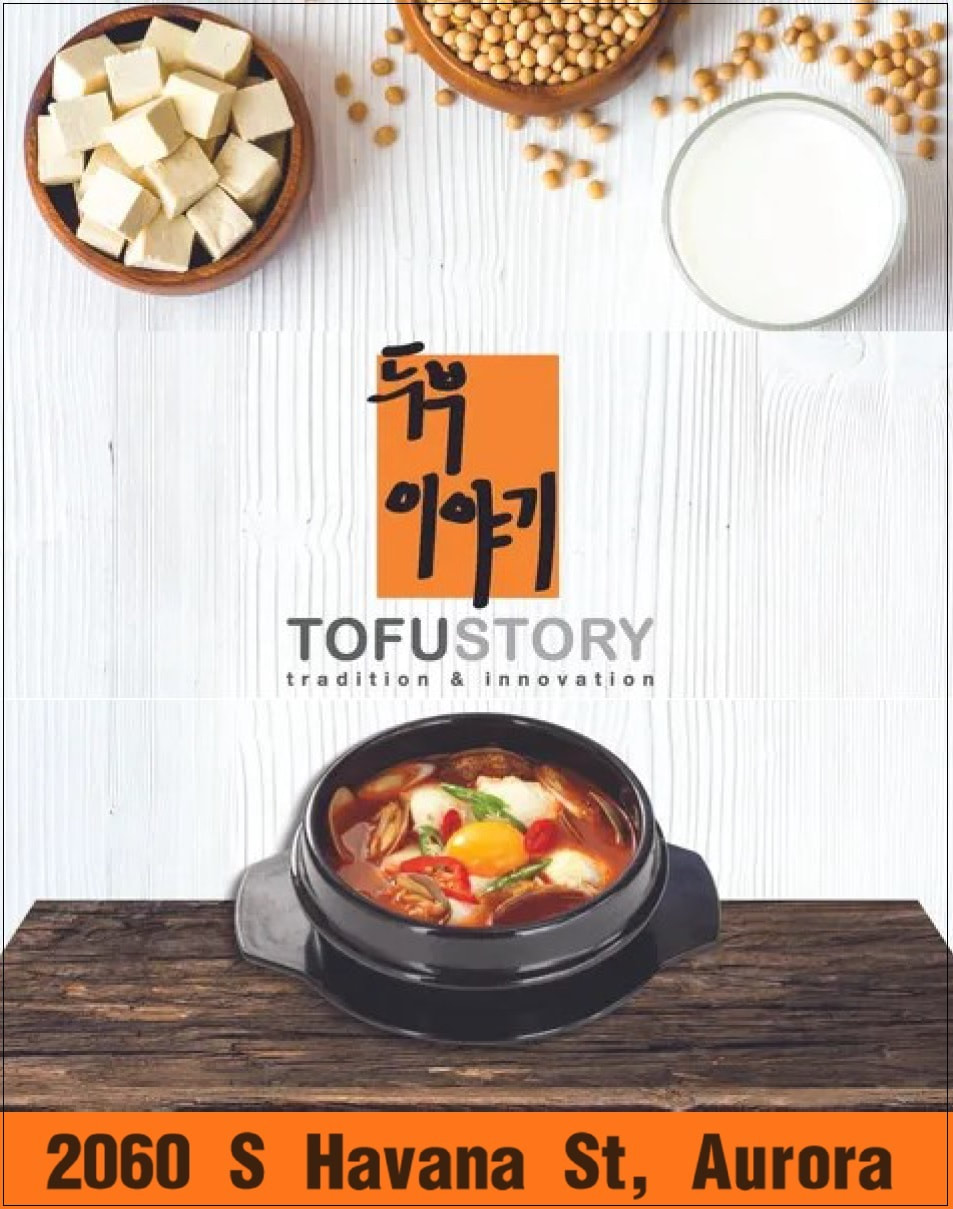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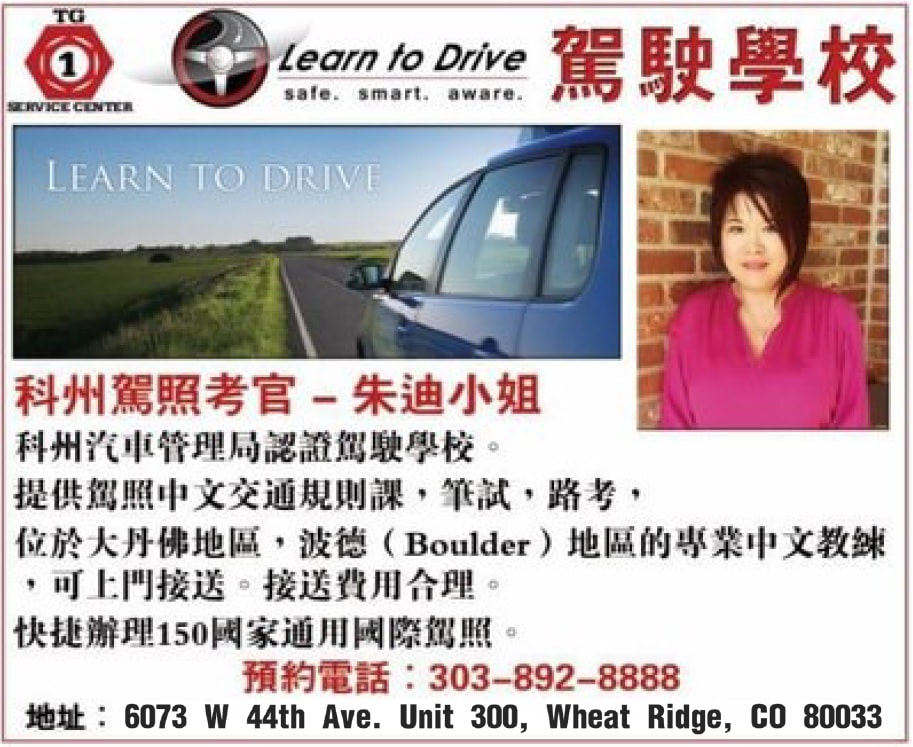

 RSS Feed
RSS Feed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