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感谢方诺女士分享短文作品“移植的菊花脑”
对她而言,菊花脑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在南京,每年夏天哪家不是每个星期都要吃上好几回?漫长的火炉似的南京的夏天,还有什么能比菊花脑汤更消暑?碧绿的菊花脑间,漂浮著灿黄的蛋花儿,每每让她想起玄武湖碧波间的莲花。喝上一口,若有若无的凉意蜿蜒而下,宛如玄武湖畔随风轻摆的杨柳,说不出的清凉,适意。即便这样,菊花脑也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墙角路边,一蓬蓬的,菜场里几分钱一大篮。只不过也没有哪年夏天饭桌上少了它,南京人嘛,哪有夏天不吃菊花脑的? 是1985年的夏天吧,在台湾的舅舅绕道日本,回到故乡。久别重逢,泪眼相对,兄弟姐妹们不知怎样做,才能表达出和分别近四十年亲人重逢的欣喜,唯有用美酒佳肴尽心款待。可舅舅说他最想吃的是菊花脑。接下来的十多天,无论是大宴小酌,饭桌上必不可少的是菊花脑。最初的陌生过去后,她好奇地问舅舅,菊花脑真的那么好吃吗?舅舅看了只有十几岁痴迷著三毛的她一眼,想想自己从学校参加青年军,刚去台湾时,也是她这般年纪。离乡背井,躲在被子里,哭著想家,想妈妈的心情,眼前的孩子能懂吗?于是只说一到夏天,就想喝一碗菊花脑汤,想了快四十年了。即使现在每天喝,也不过二十多碗,一年一碗都不到呢。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心里仍是不解,四十年吃不到菊花脑有那么遗憾吗?舅舅回台湾时,带上了一大包菊花脑种子。希望能在后院种出菊花脑来,那么在台湾,夏天也能天天吃上菊花脑。舅舅这么说。以后每次给舅舅写信,她都会问一句,菊花脑发芽了吗?没有!没有!舅舅总是这么说。每年春天,她总会在信封里,偷偷夹一点最新的菊花脑种子。没有发芽!没有发芽!舅舅还是这么说。几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。菊花脑出了南京是种不活的。舅舅最后说。 就是那年,她也离开南京。没有故乡的泥土,当然也没有菊花脑种子,在机场出境室前,她拍拍背包里的三毛的书,对泪眼滂沱的妈妈潇洒地说:“我真的要去流浪了。”虽然最后的语音也有些哽咽,但她仍是昂著头。异乡,乡愁,流浪,在二十岁的浪漫情怀里,是诱惑的。自然她要飞去的不是窄窄的海峡对岸,而是千山万水之外的大洋彼岸。 异邦的生涯是从中部的大学城开始的。那半年冬季,半年夏季的小城总是如死水般的绝望。在第一个漫长的冬季里,往日的天真,活泼,无忧的她就被一层又一层的白雪覆盖,冻僵,死亡。在初春新绿中偶尔发呆的她,想起在故乡的种种,竟似前尘往事般模糊。是不是那些事曾真真实实地发生过?不止一次她在沉入梦乡前的朦胧中问自己,而梦中,在飘忽不定中最真切的是中山路上的梧桐绿和那一行行的泪水。 往后的日子沿著预定的规迹滑行著。毕业,工作,拿绿卡,没有意外,也没有惊喜,一切都是顺理成章。曾几何时,梦中的绿色梧桐模糊成若隐若现的影子。 欣喜中,期盼中,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,往日记忆随著熟悉的乡音在熟悉的街道里一点一滴聚拢,但记忆怎么也追不上变化的脚步,故乡已还原不出记忆中的模样。熟悉的街道中,夹杂著不熟悉的高楼,熟悉的乡音里,有她听不懂的词汇。喜出望外的父母对她客气的有点生分,在熟悉的家里被细心照顾的她,有著作客的感觉。她希望听到妈妈说:“快下楼买菜”,而不是妈妈小心翼翼地问:“今天想吃什么?”她如何也无法相信,可也不得不承认,时间和空间会改变一切,在那一刻,她明白了什么是咫尺天涯,本以为会有满腹的话向妈妈倾诉,本以为还会象以前一样赖在妈妈身上撒娇,她却是什么都说不出,什么都不想说,在故乡二十年的岁月是前世,而在异乡的她是再世为人。她只是喝了一口菊花脑,凉凉的,凉凉的。菊花脑汤依然有著记忆中的鲜美清香。身在故乡的她,觉得故乡离她好远好远。 买房子了。她对老公认真地要求辟一块菜地,老公看著瘦弱的她,满脸疑惑地答应了。对种地这回事,她表现出罕见的执著。选一块地势和采光最好的地,挖掉绿油油的草坪,细细地把地翻了又翻,小心地撒下种子,那种子是妈妈夹在信中寄过来的,那是菊花脑的种子。在忐忑不安中,她盼著菊花脑的出苗,发芽,在患得患失中,她终于能体会舅舅的心情。她提笔给舅舅去信:你在异乡是无奈,我在异乡是自愿,可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?我们同是游子。在对故乡不变的回忆和故乡万变的现实间,我们同样是不知所措,菊花脑成了唯一不变的寄托。而一年又一年,希望又失望,菊花脑终于没能长出来。也许正如舅舅所说的,离了故土的菊花脑是没法生根发芽的。可不管怎么样,她每年春天仍抱著一线希望,翻地,撒种,是一种坚持,是一份宣言,也是一个信念。 突然有那么一天,在白栅栏围著的小菜园里,竟奇迹般的出现了一点娇弱的嫩绿。被失望折磨了几年的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冲到近前仔细端详,是的!是的!是菊花脑。终于发芽了,终于在异国的土地上发芽了。她兴奋地狂奔上楼,边跑边叫:“老公,菊花脑发芽了!菊花脑发芽了!”老公急急地冲出来:“小心点!你怀著孕呢!”是啊,她幸福地抚摸著自己的肚子,一个崭新的生命正在悄悄地成长。 可以申请公民了。她不加思索地象平常处理公事一般,填表,寄支票,心中没有一丝涟漪。宣誓的那天,在一片欢天喜地的气氛中,她却不明所以的郁郁寡欢起来。举起右手,跟著移民官喃喃地念著誓词,她忽然觉得万分委屈,眼睛也潮湿起来,一种被遗弃感觉。怎么像是被亲生父母过继给了别人。干什么你,她对自己说,是你选择放弃生你养你的故土,你有什么好委屈的。虽这么想,可开车回去的路上,她还是觉得心里堵得厉害。回到了办公室,她惊讶地发现她的办公桌已被同事们用红,白,蓝三色彩带和花环装饰起来,一瓶香槟上插著星条旗,一张贺卡写满了同事们祝贺的话。同事们还说,大家订了个大蛋糕,中午在休息室大家要为她庆祝。她不是没告诉别人吗?只是昨天向老板请假时提了一句。她眼睛又潮湿起来,一时间,说不清是感动,还是感伤。 清清楚楚的,她又走在熟悉的大院里,一楼的沈妈妈如往常一样,从厨房的窗户里探出头:“大姑娘回来啦?”“哎!”她答应著。仍是昏暗的楼道,仍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,她走著一级又一级的楼梯,心中一片平和,家,温暖的家在六楼上。她忽然间清醒了,朦胧的天光中,枕边是一张甜美的小脸。她撩起窗帘,后院,菜园,晨光里的菊花脑显得生机勃勃。她的泪潸潸而下:菊花脑,移植的菊花脑。 Comments are closed.
|
Archives
July 2024
|
此网页所有版权为丹佛华人资讯网所有。 有对网页有关的问题请于[email protected]联络网页编辑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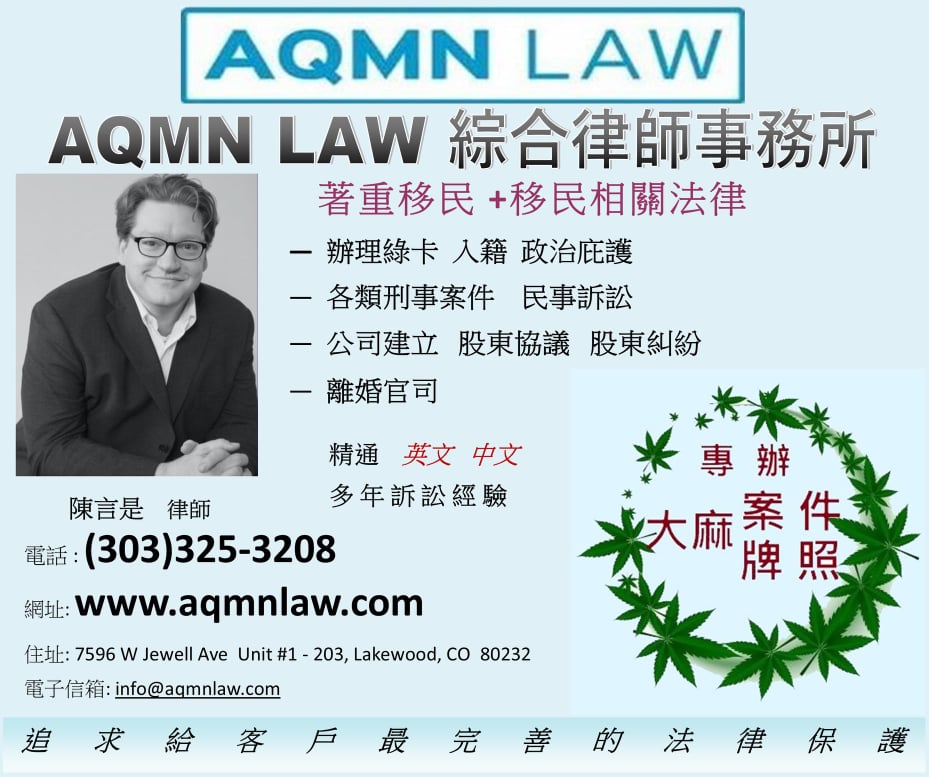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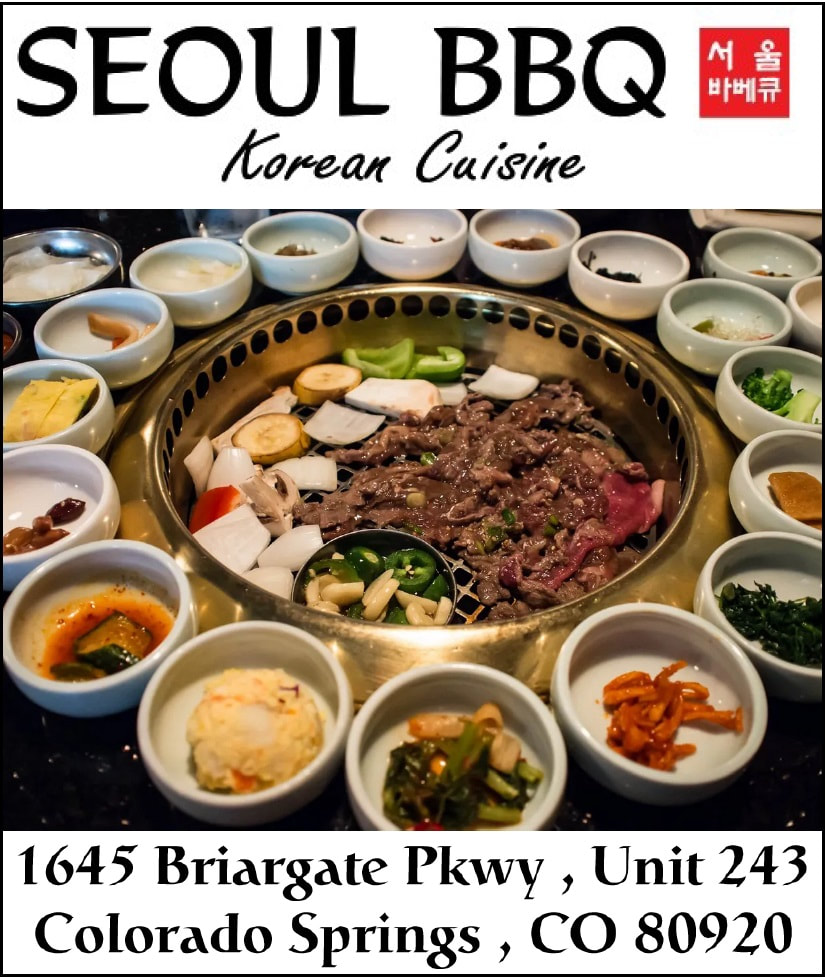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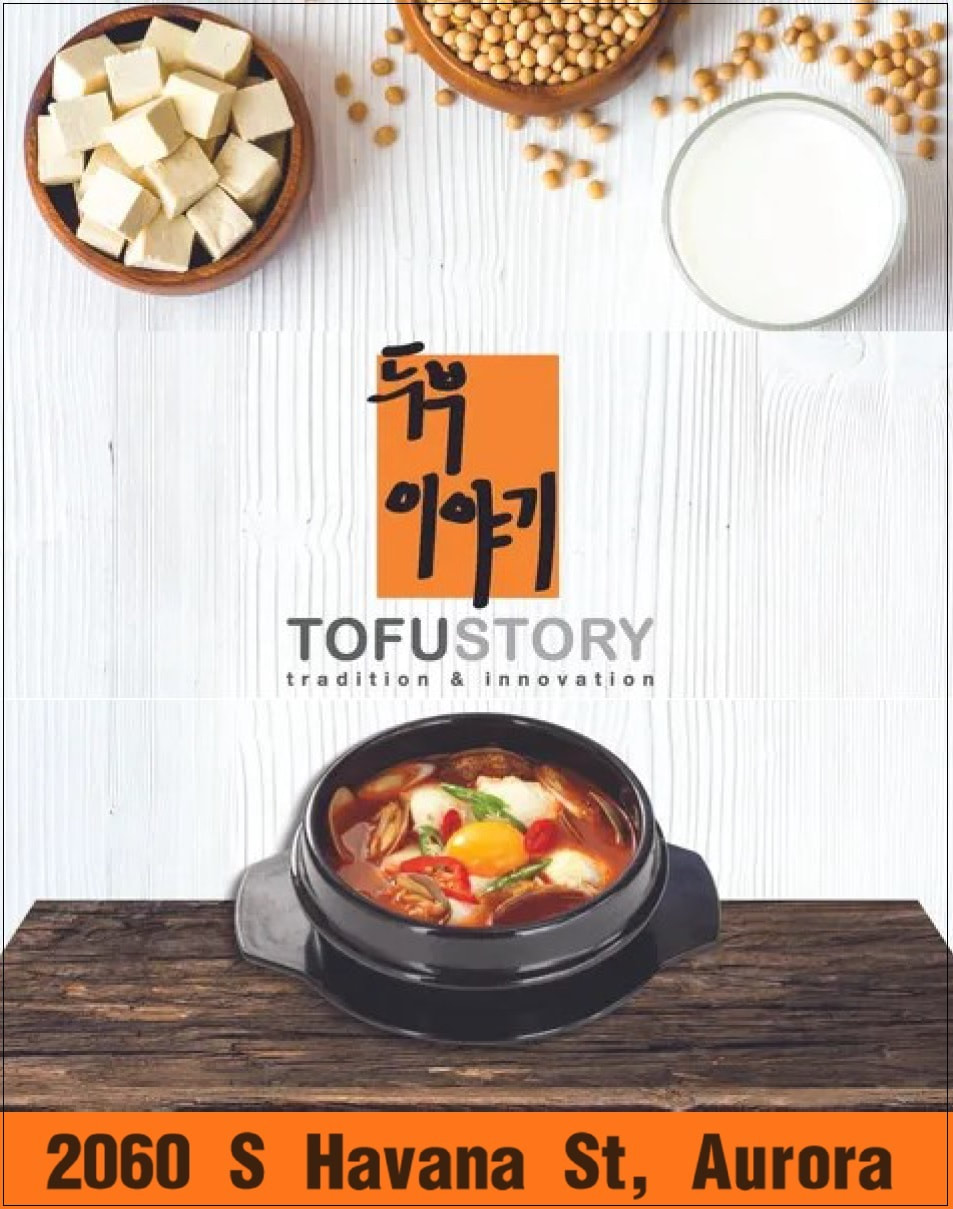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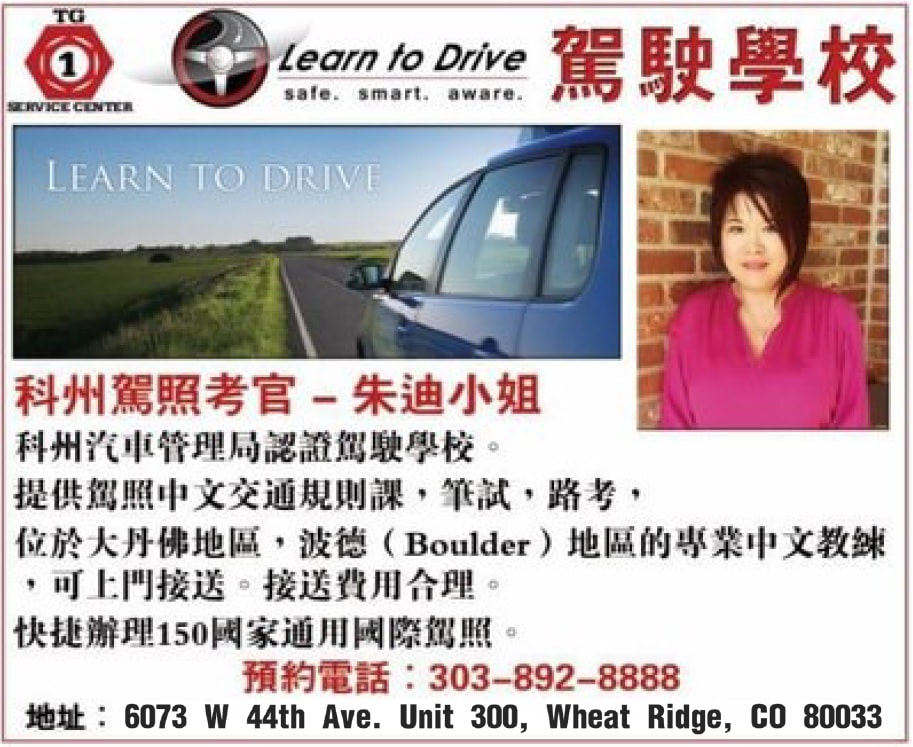

 RSS Feed
RSS Feed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