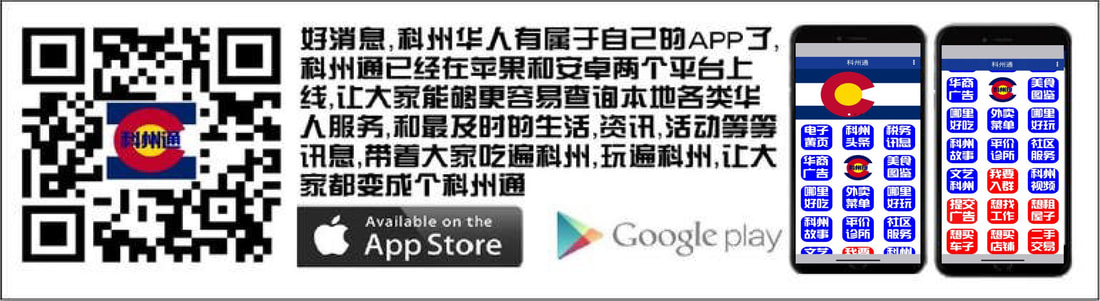|
感谢吴纪珍女士分享短文新作“宋代苏轼的诗词之美”
「三过平生堂下,半生弹指生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。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弔文章太守,能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。未转头时皆梦。 」此诗写于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,距今约940年前;是宋代苏轼东波居士第叁次到扬州恩师欧阳修于1048年时所建的「平生堂」,同时也感叹人生自身的遭遇。苏轼共叁次到过扬州,第一次,是熙宁四年(1071)由京赴杭州任「通判」一职(此官位始於北宋时期直到清朝灭亡後被废除,任务就是监督州长或省长以防止他们职权过重,专擅作大,也是朝庭爲加强对地方官的控制),南下经过扬州;第二次是3年之後的熙宁七年(1074)由杭州移至密州,北上时途经扬州;第叁次是丰二年(1079)从徐州移至湖州(今浙江省吴兴)。在这8年间,苏轼叁过「平生堂」下,实质上浓缩了他近10年间南迁北调的动荡生涯,此时42岁的他想起自己官场坎苛,嚐尽人间冷暖,感慨岁月蹉跎,人生如梦,恩师虽然过世了,活得人又何嚐不是在梦中。於是藉由这首诗来提醒自己,治政权力与荣华富贵皆是短暂人生中的梦幻泡影,用此来平复与抒发他的仕途遭遇,看淡功名,笑看人生。 在政治上,於王安石变法期间,苏轼虽赞同政治应该改革,但反对王安石任用的後任吕惠卿及ㄧ些不好的政策,招来新党爪牙李定横加陷害;後来又因反对「尽废新法」受到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斥退,於是终身当不了宰相,壮志未酬。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导致官场失意。 这首西江月(平山堂)的译文是这样的:我第叁次经过平山堂,前半生在弹指声中过去了。整整10年没见过老仙翁了,只有墙上他的墨迹,仍然是那样气势雄浑,犹如龙飞蛇舞。我在平山堂前「欧公卿」的下面,写下这首诗悼念,文坛英杰,故扬州太守欧阳修。别说人死後万事皆空,即使活在世上,也不过是ㄧ场大梦呀! 「人生到处知何似?应以飞鸿踏雪泥;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;往日崎岖还记否,路长人困蹇驴嘶。」此诗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诗。诗中苏轼重遊河南省渑池,借宿在同一所寺庙内,想起兄弟俩曾在寺庙的墙壁上题诗,但如今庙里的老和尚已经过世,兄弟俩人题诗的墙壁也崩坏了。苏轼在诗中描述著:人生的遭遇,就像飞雁踏过雪地留下的瓜印一样,是那麽地偶然,鸿雁飞走後,没有人知道牠的去向。老和尚奉闲已经去世了,他留下的只有一座藏骨灰的新塔,当时提的诗句,也因爲墙壁损坏,再也找不到诗的遗墨了;还记不记得崎岖旅程吗?路又远,人又疲劳,驴子也累得直叫。宋仁宗嘉佑六年(1061)十二月,苏轼赴任陕西路凤翔府签判(宋代签字允发判官一职),路过河南渑池。苏轼的弟弟苏辙送哥哥到郑州,然後返回京城开封,但眷念手足之情难遣,於是也写下『怀渑池寄子瞻兄』寄赠。诗是这样写的:「相擕话别郑原上,共道长途怕雪泥。归骑还讯大粱陌,行人已度古崤西。曾为县吏民知否,旧宿僧房壁共题。遥想独游佳味烧,无方骓马但鸣嘶。」,原译:同行兄弟在郑原野上话别,共同担心前路艰难。骑马回头仍在大粱田间巡行,想到远行的哥哥已经翻过崤西古道了。曾经做过渑池主簿(文书主管)百姓知否?还曾和哥哥歇宿僧房共题壁诗。远方思念哥哥在旅途寂寞地独行,茫茫的路途确只能听到骓马(战马)的嘶叫声。苏东坡面对人生的波浪、际遇的曲折,由於兄弟情深,使得东坡寄语家弟时,能够灵犀相通,抒发内心的感怀。 「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千里孤魂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」苏东波这首「江城子」是追悼他的妻子王弗之作品。语译:漫长的10年,两人死生茫茫永隔,即使儘量不去想它,确仍是难以忘怀。 妳的孤坟,远在千里之外,我无处能向妳倾诉,实是满腹的凄凉与悲伤。纵然妳我再相逢,我这10年来四处劳苦奔波,已是风尘满面、两髮鬓白如霜,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。深夜里我做了个幽然的梦,恍惚回到了家乡,年轻的妳正坐在闺房窗前梳妆,妳我对望却无以言对,只有流不尽的千行泪水。可想得到,每当忆起那一轮明月照映著妳坟碑上长著矮松的山冈时,就是我年年苦痛断肠的地方.....。这首诗写於公元1077年,也就是苏轼40岁那一年,妻子10年的忌日,诗中充满感人催泪的词语,即使在942年後的今日,读起来仍令人感动不己。 苏轼在中国的文学史上,有极高的成就。除了绘画,他在文章、诗词、书法方面也极富盛名,在词坛上有「豪放派始祖」的美称;与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和曾巩共称「唐宋八大家」。 在今日现代忙碌的生活中,能在宁静的早晨阅读一些苏东坡在900多年前写的诗词作品,透过作者语中的情感流露,和现今的你我实无差异,东坡的诗词不仅是万世流芳,也是人类真性情中最优美的对话.....。 Comments are closed.
|
Archives
July 2024
|
此网页所有版权为丹佛华人资讯网所有。 有对网页有关的问题请于[email protected]联络网页编辑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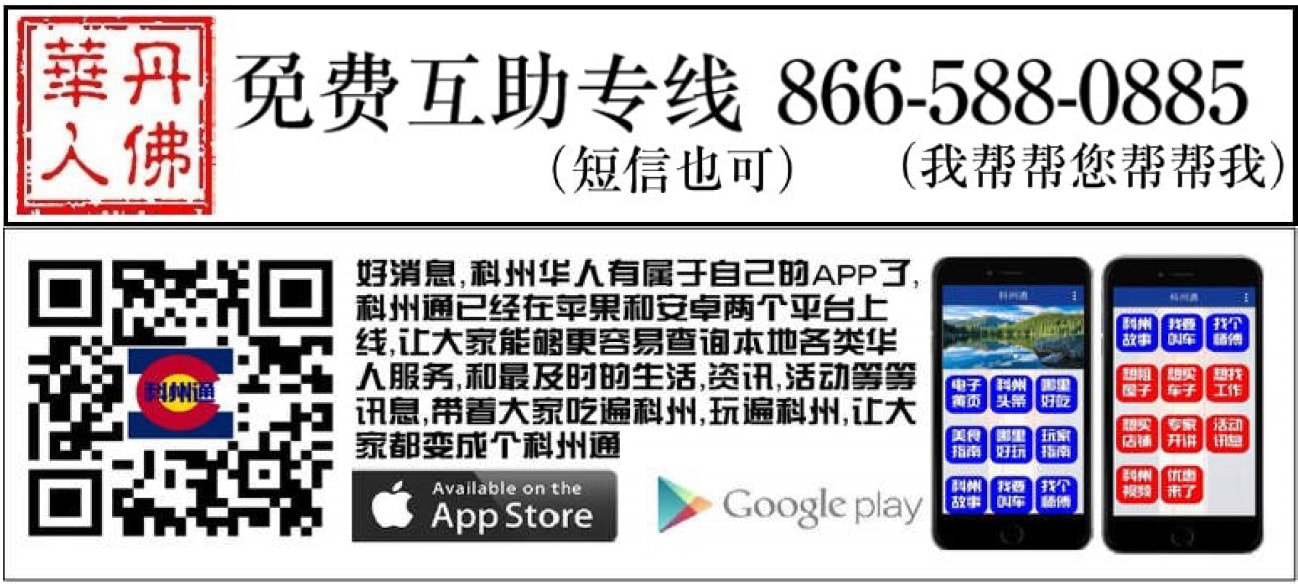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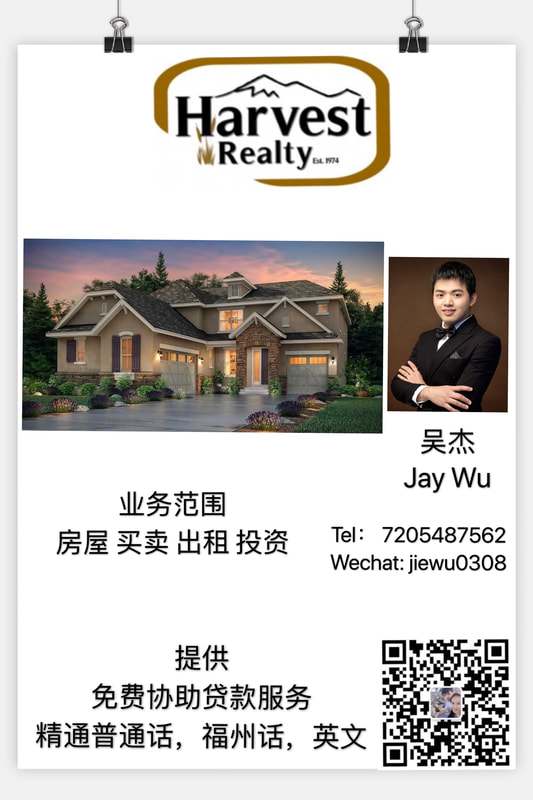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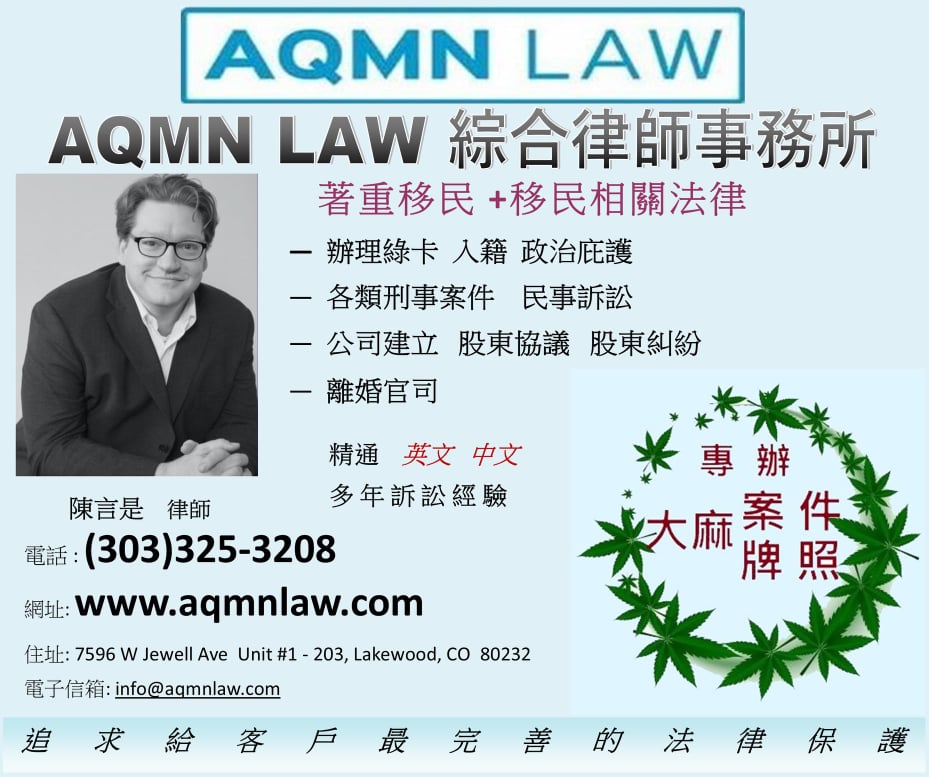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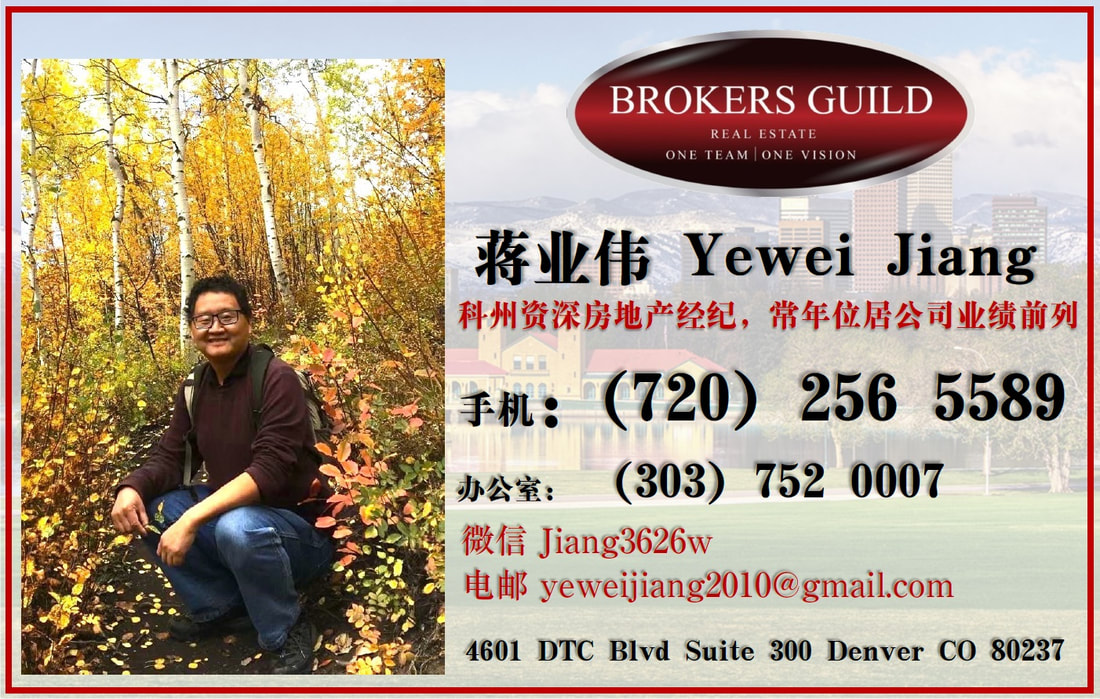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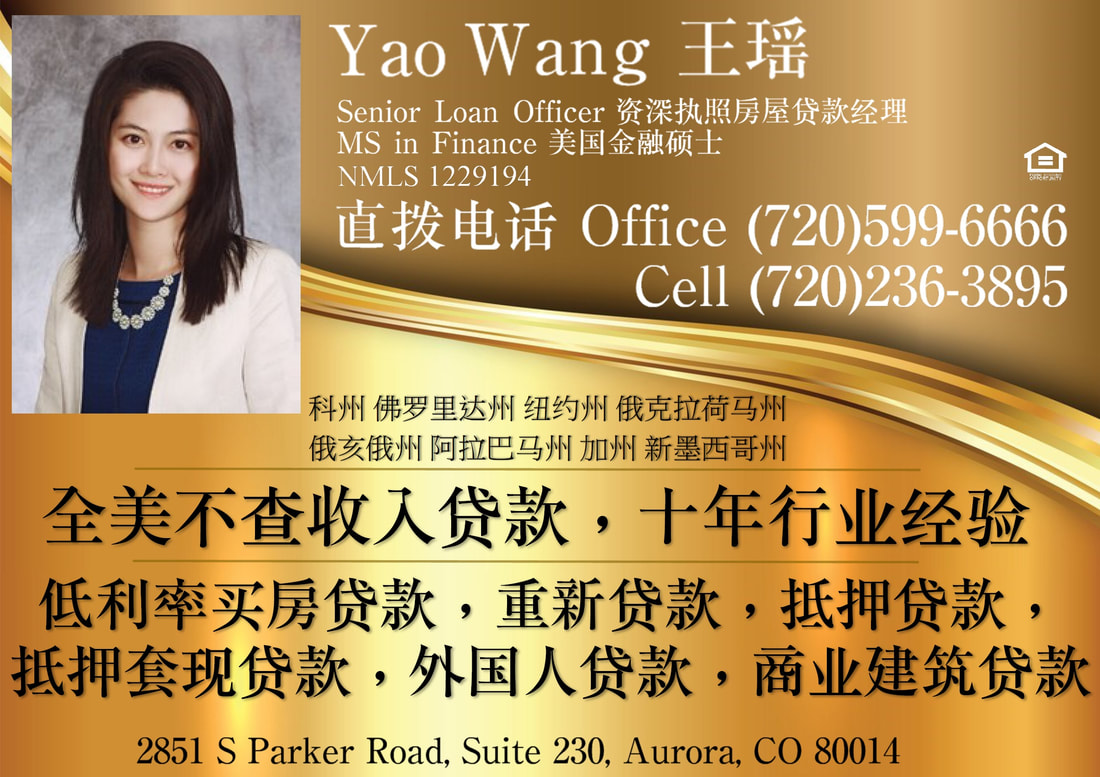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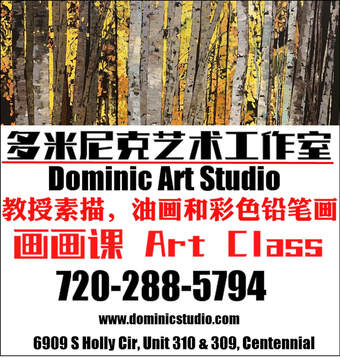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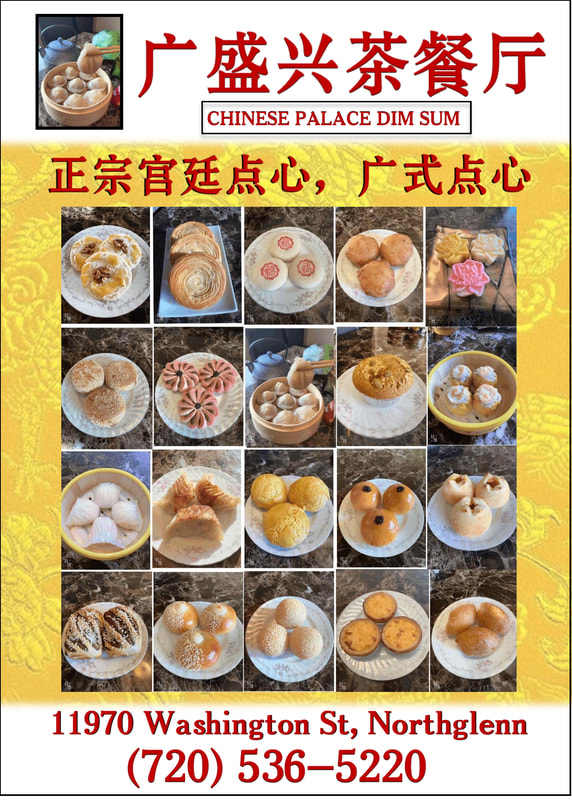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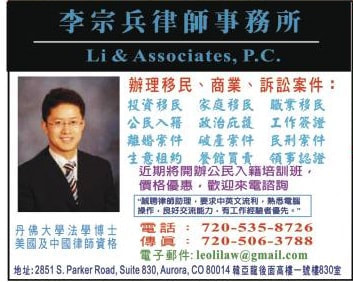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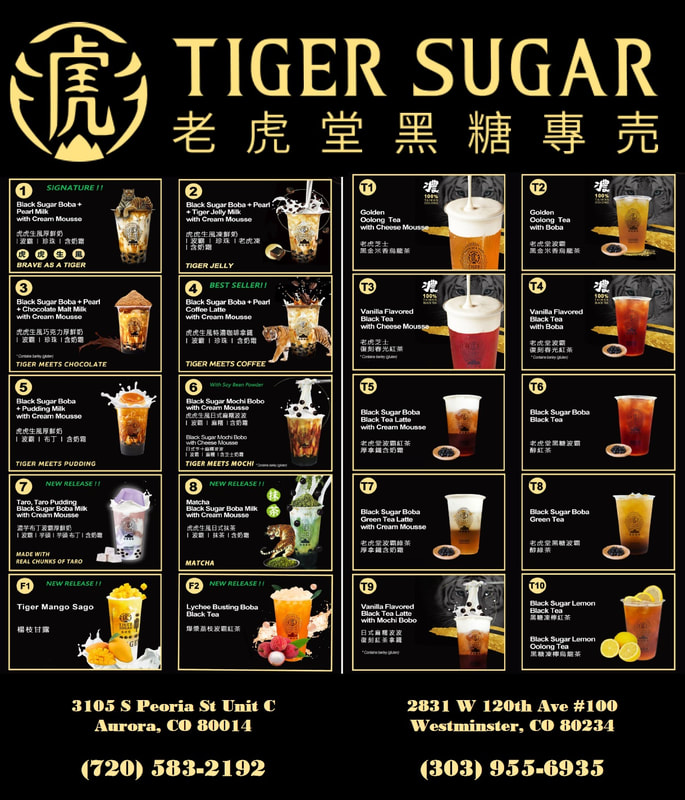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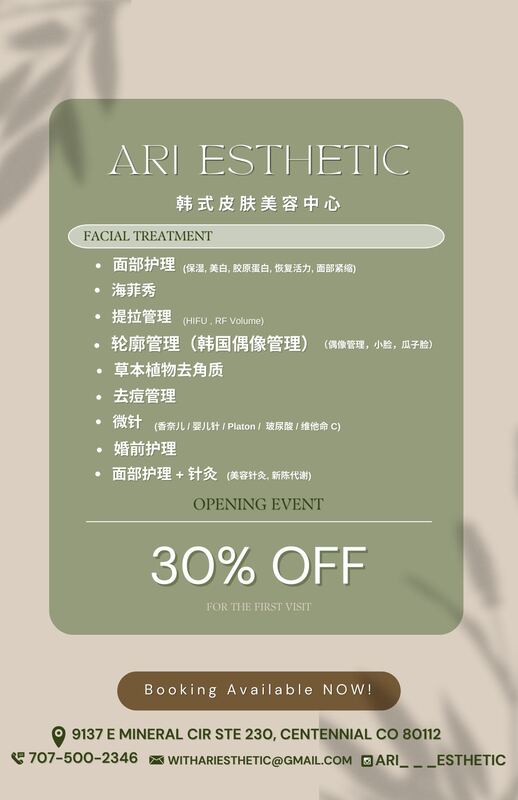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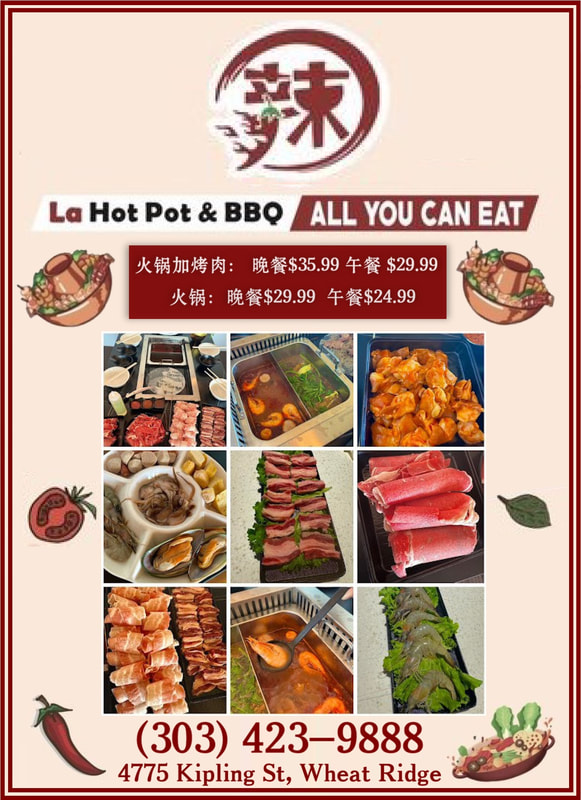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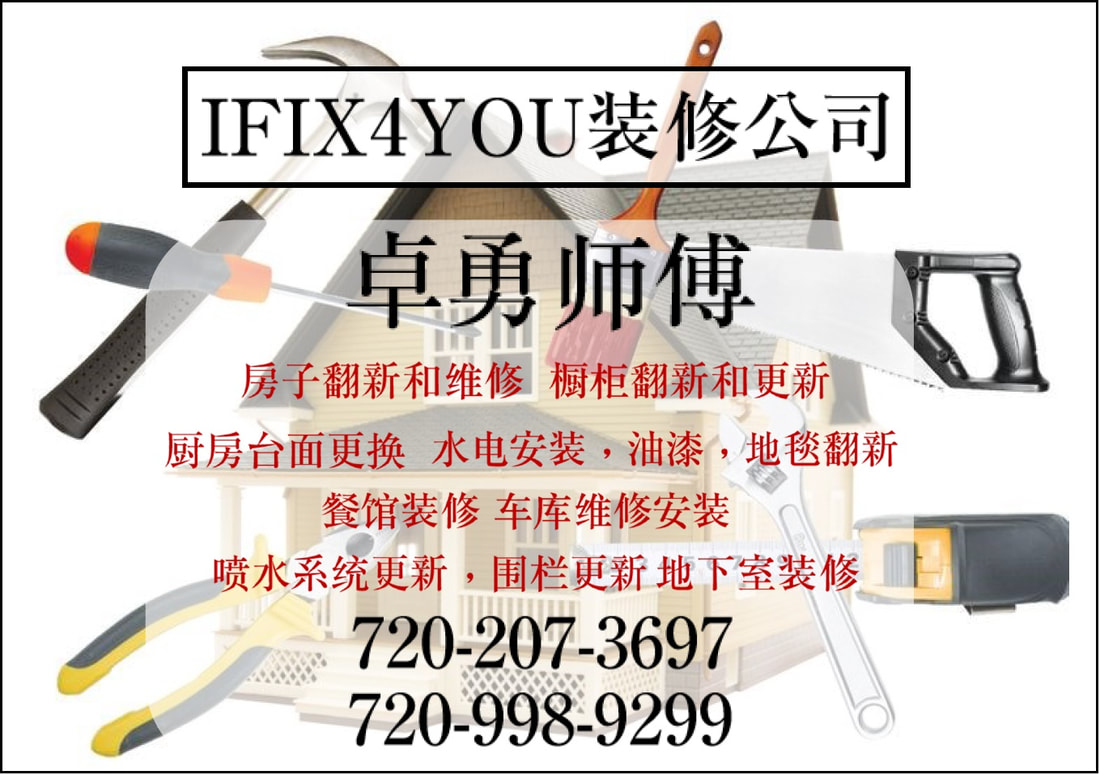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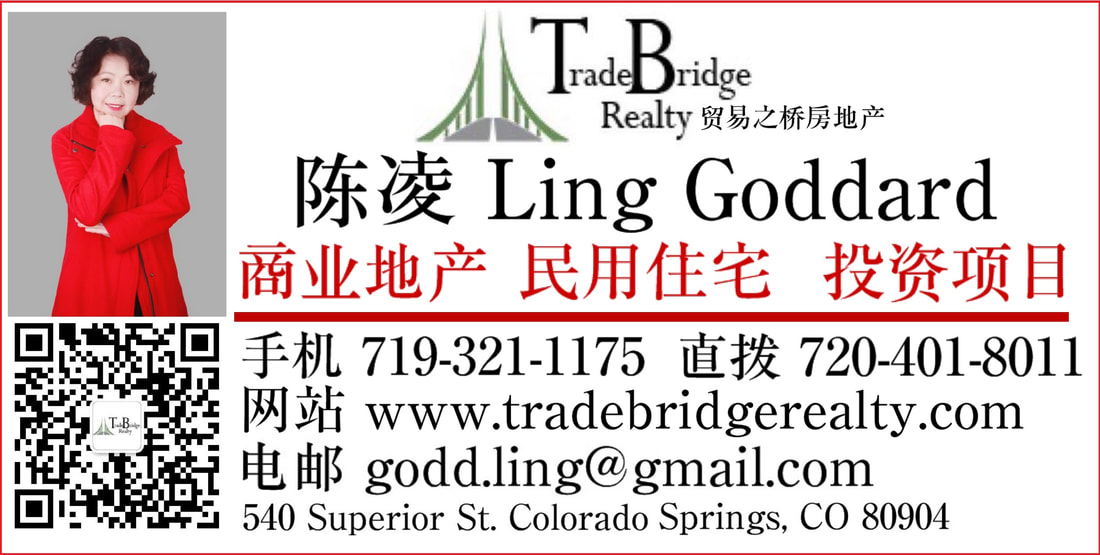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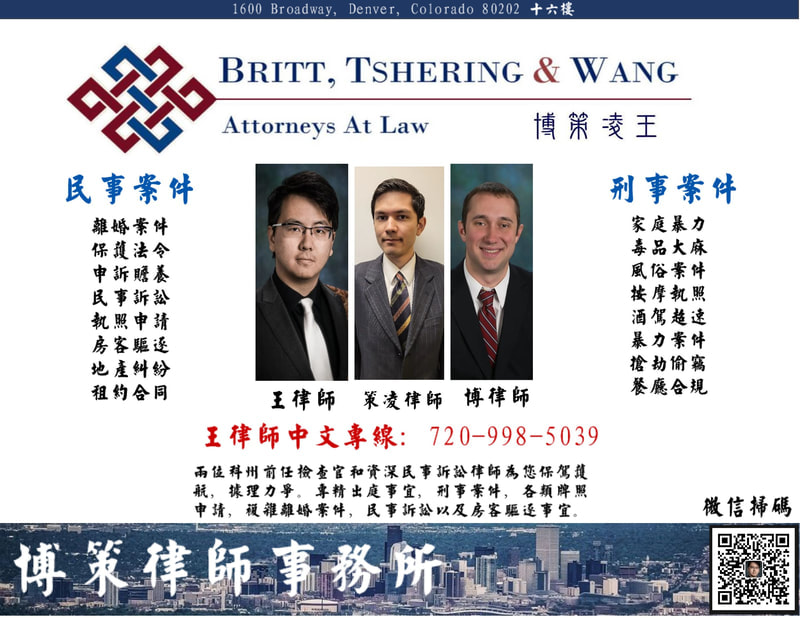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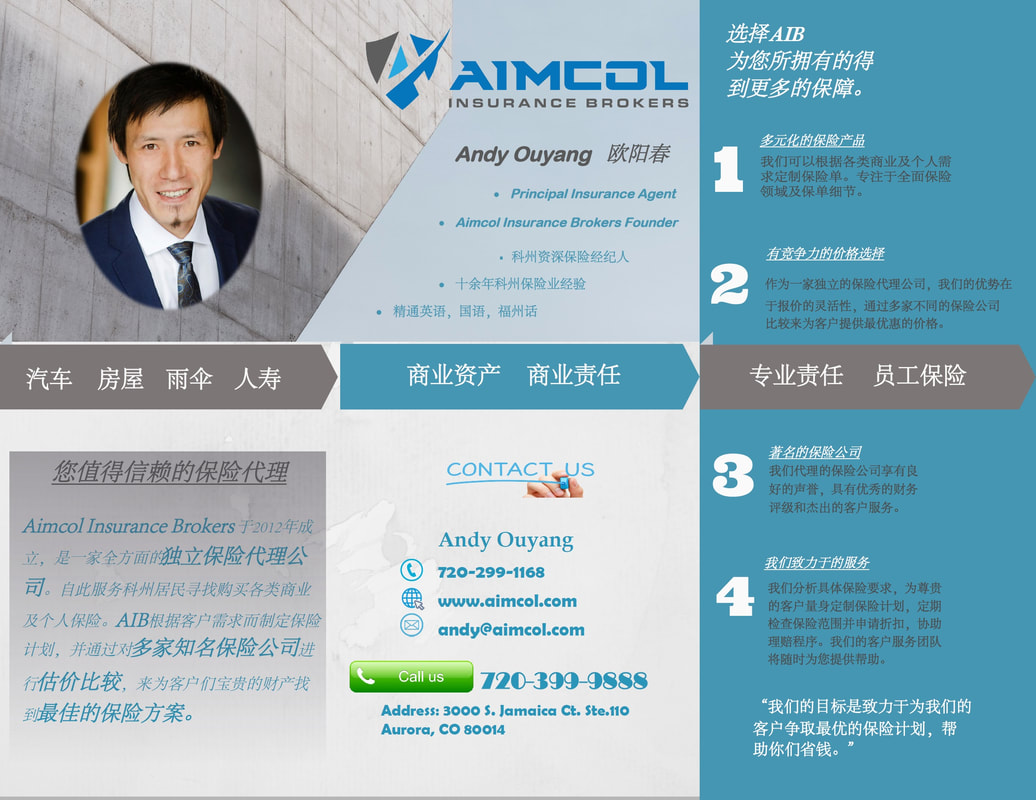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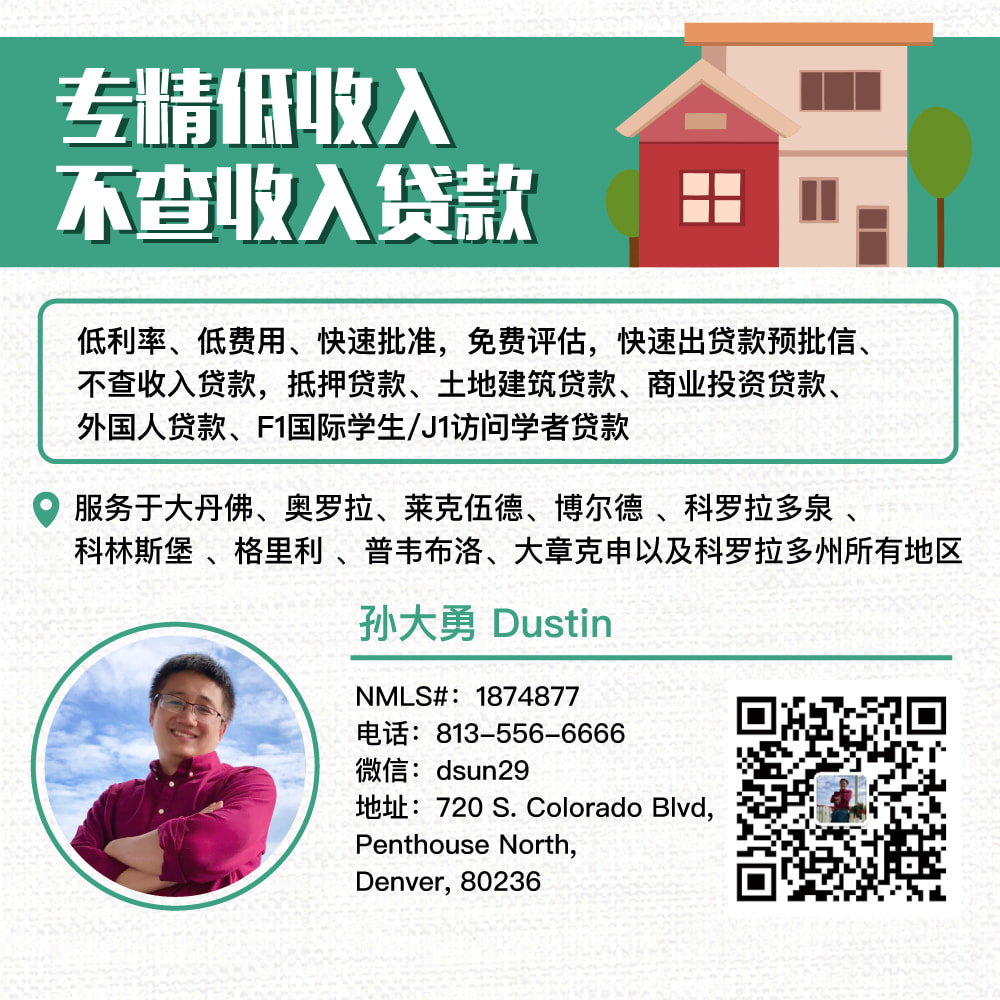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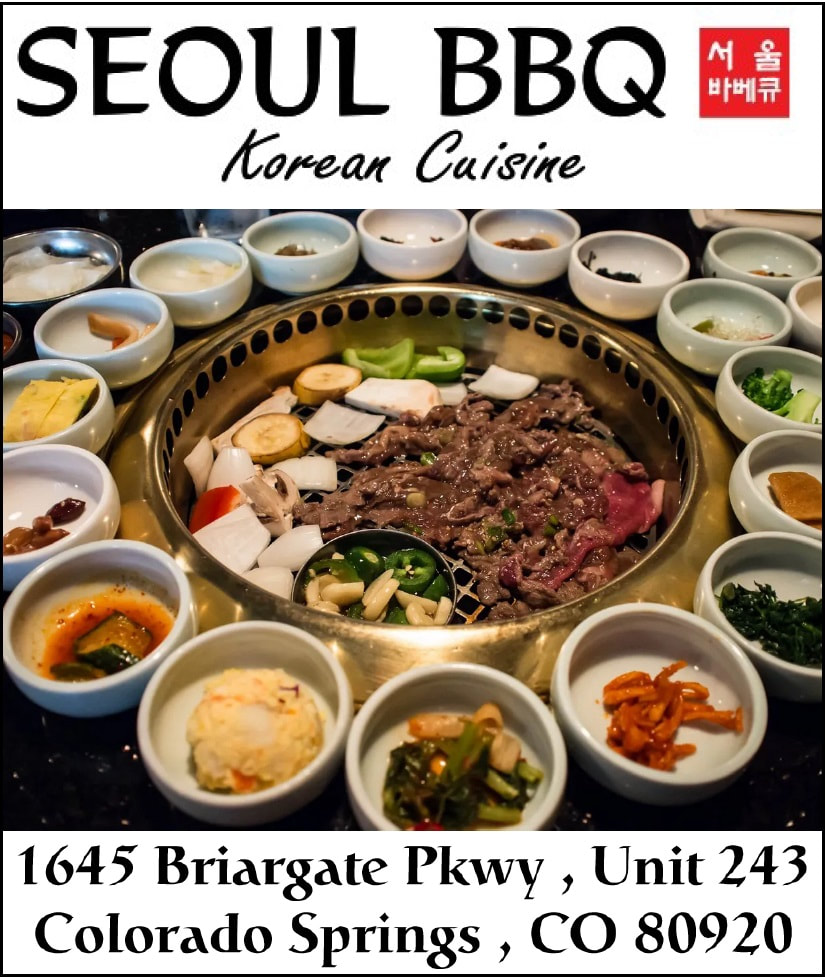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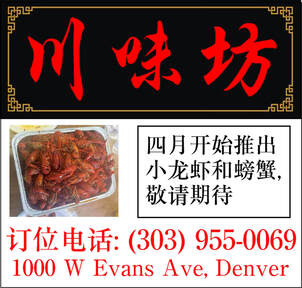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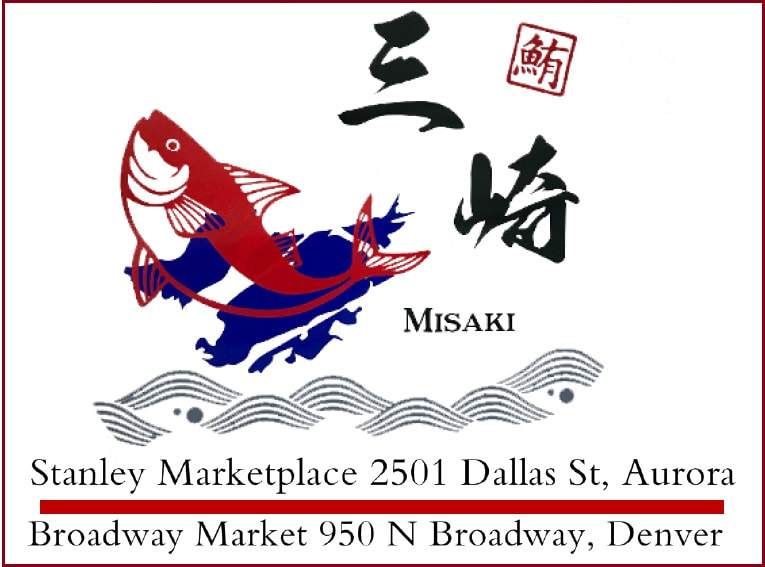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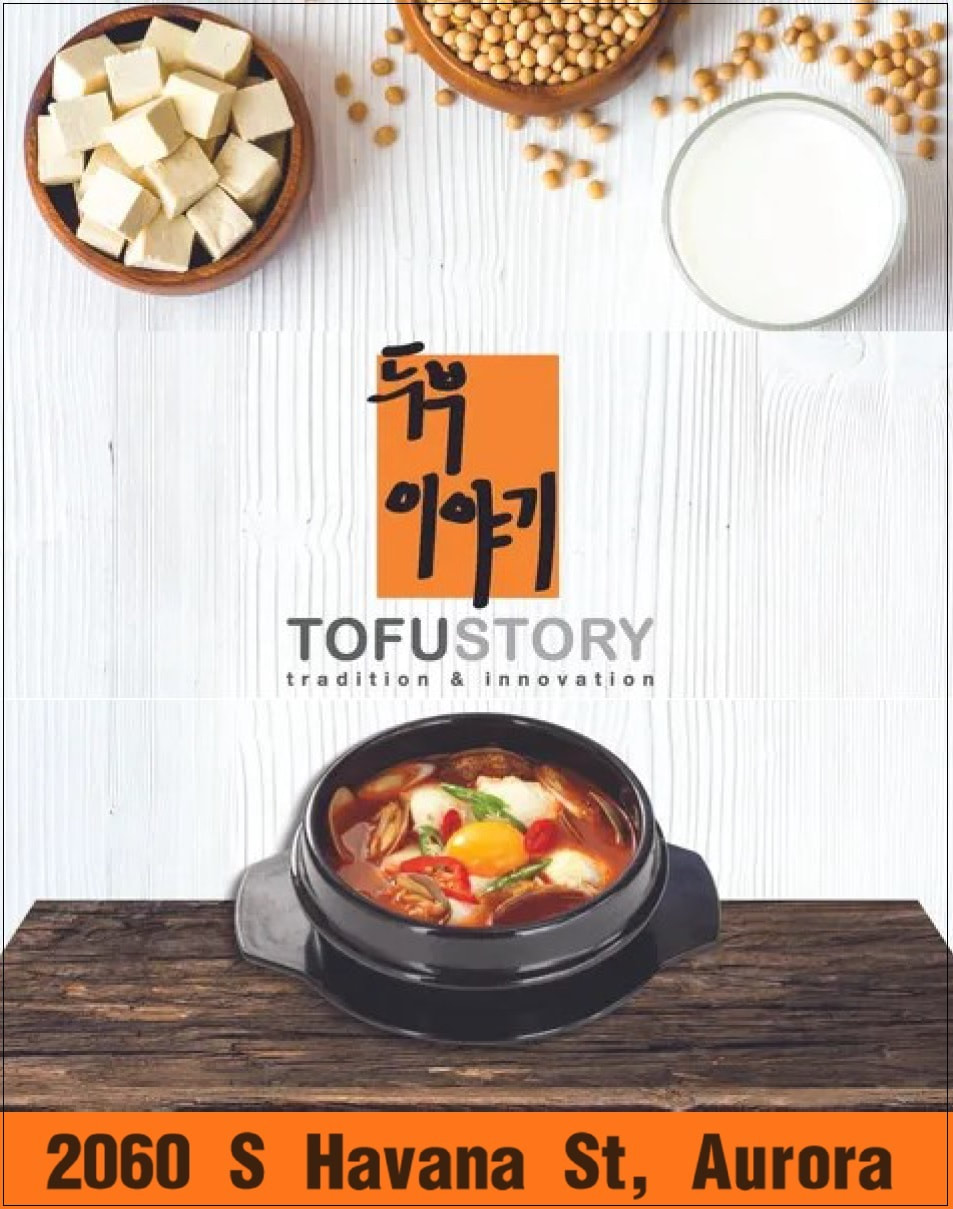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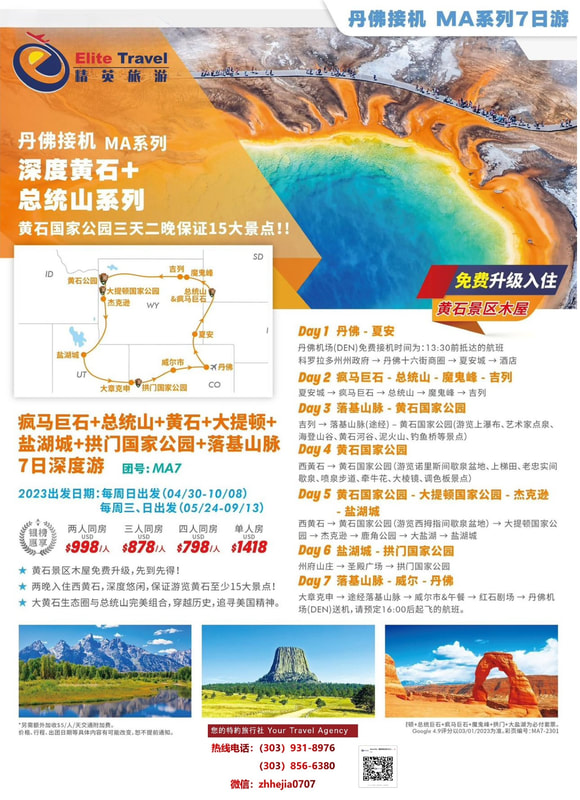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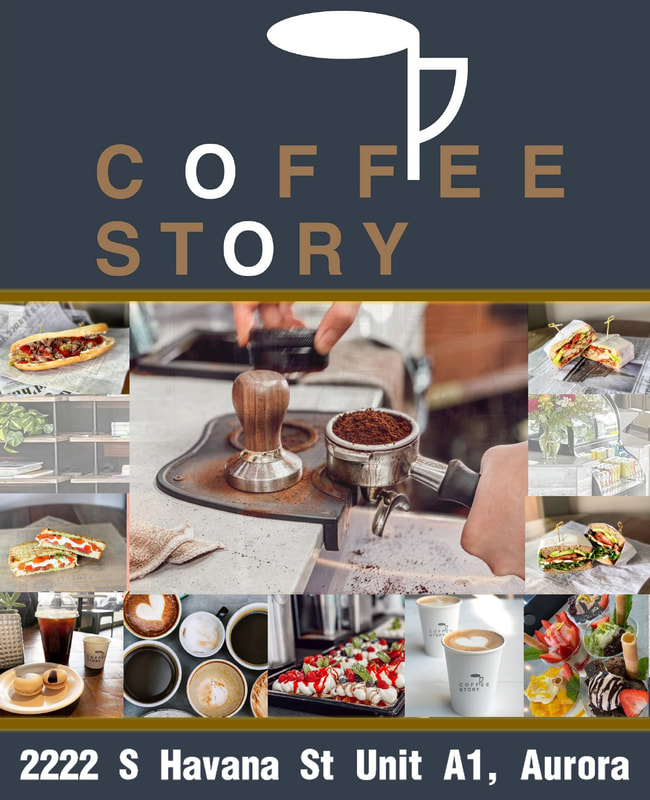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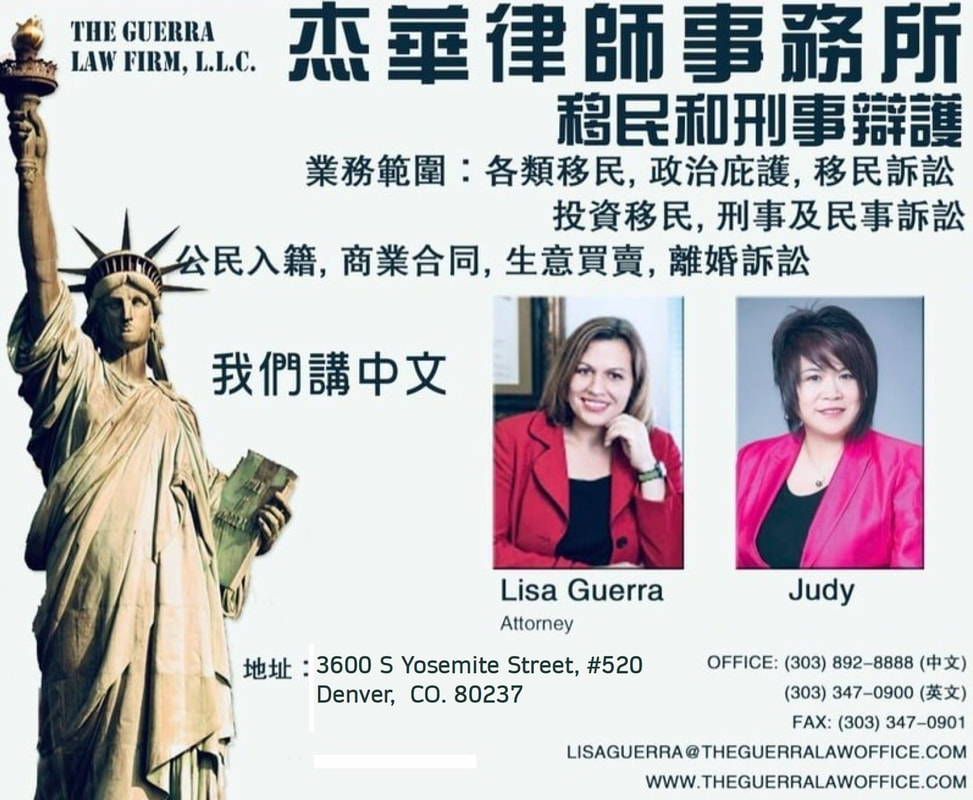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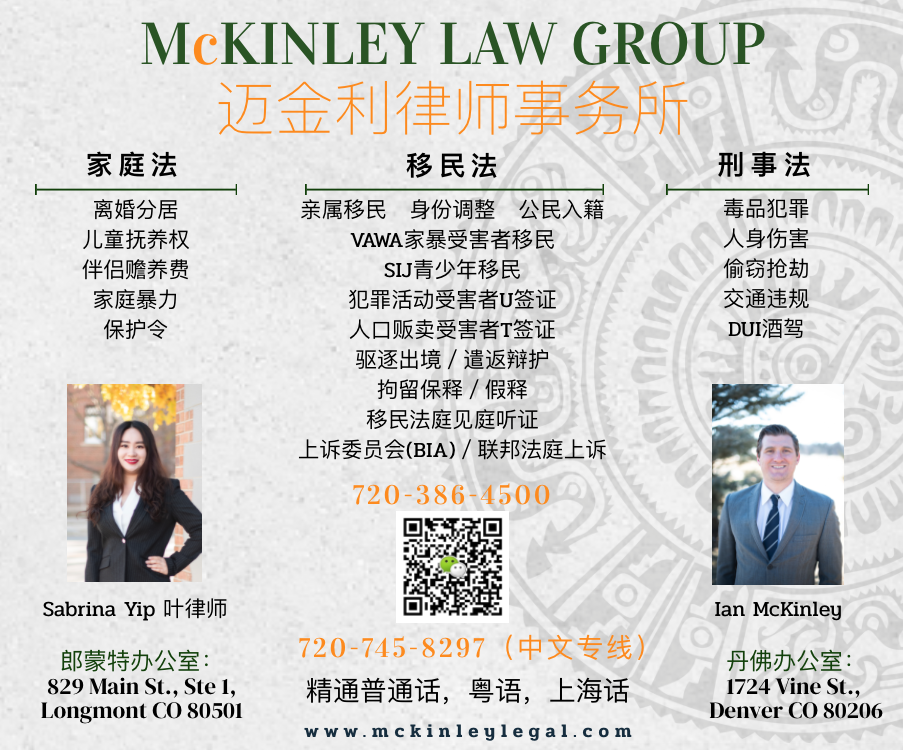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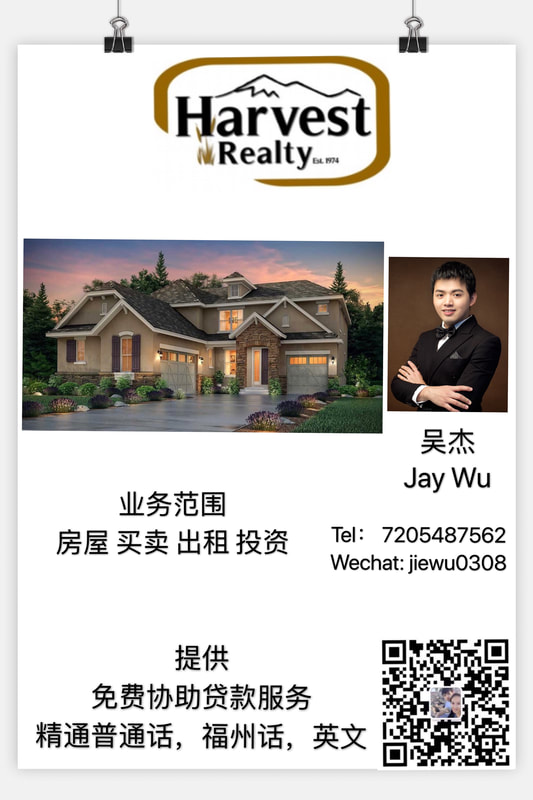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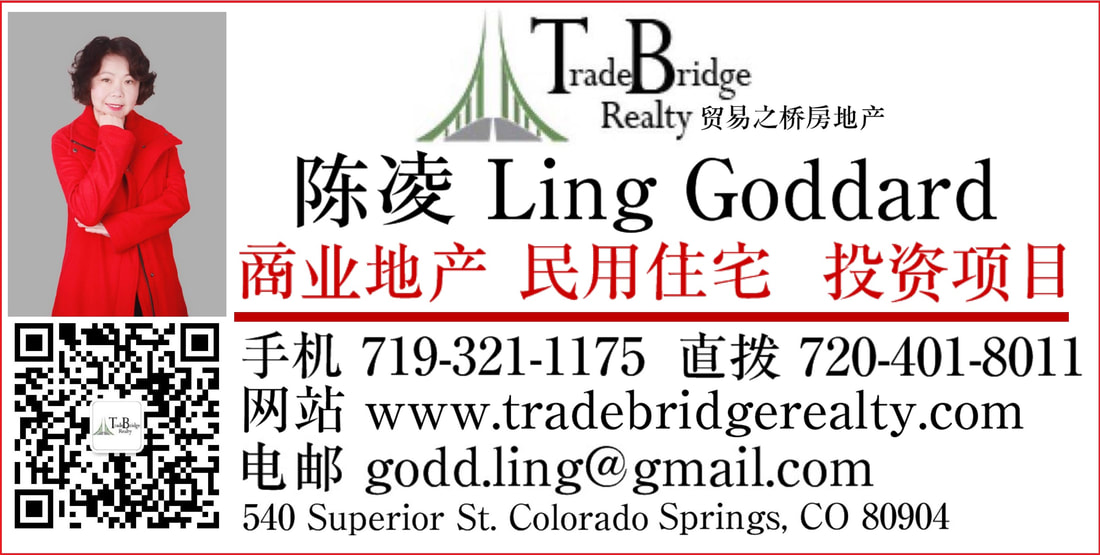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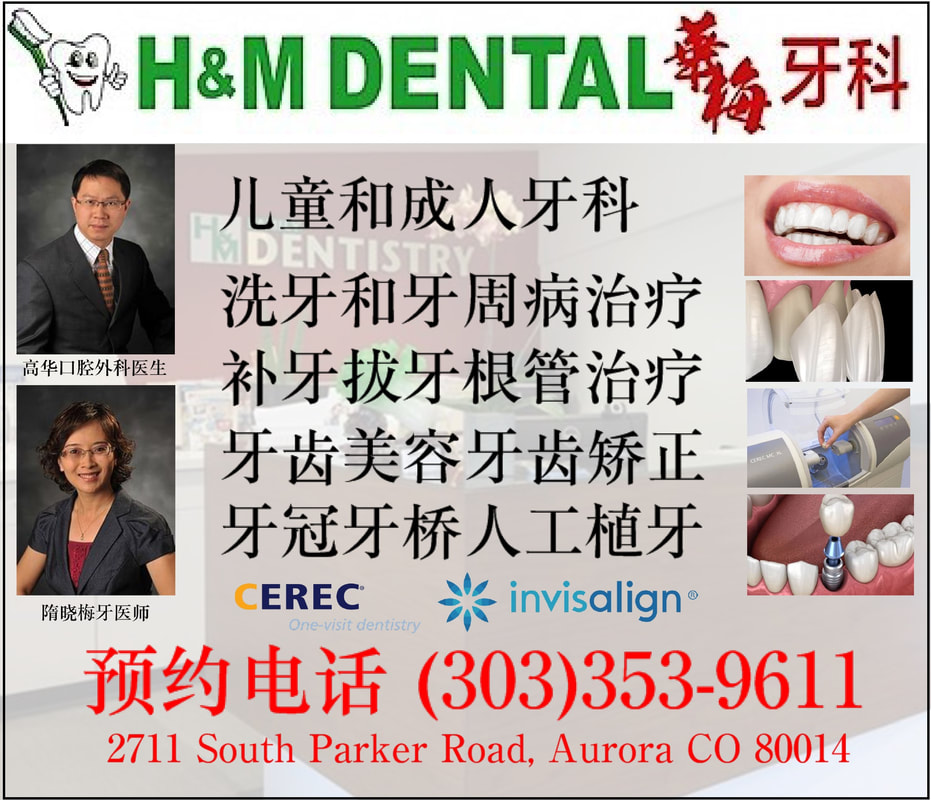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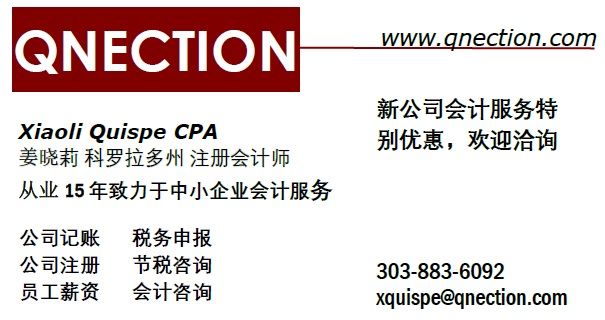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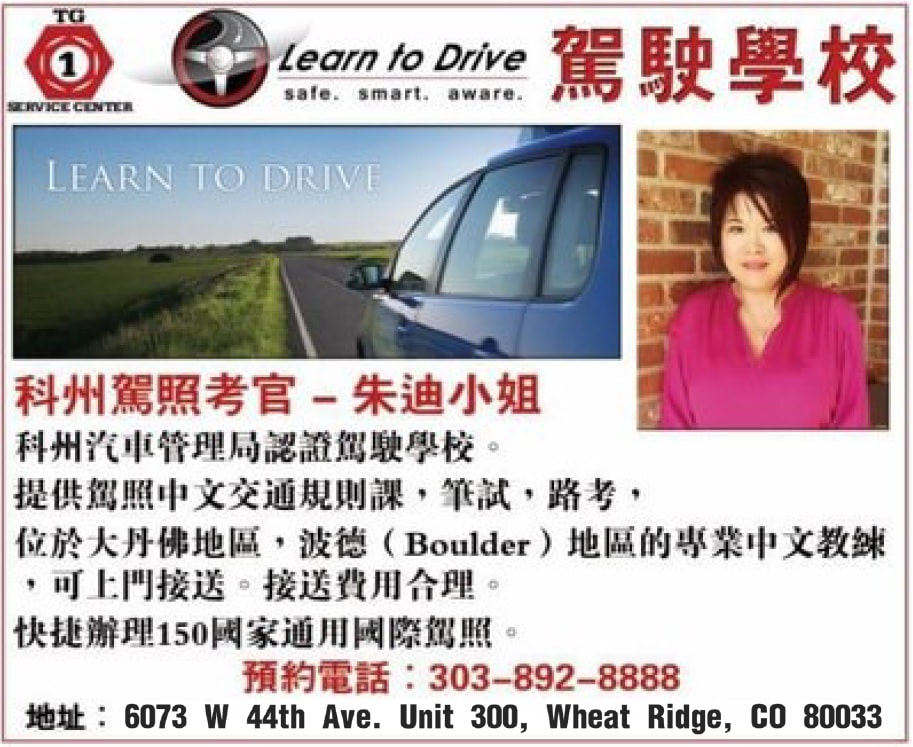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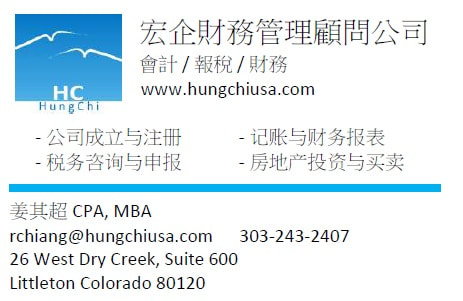
 RSS Feed
RSS Feed